最高法发布指导案例
划定数据权益的司法保护边界
2025-09-04 13:56:12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此次案例发布覆盖了从数据集合的经营性利益,到企业数据的加工使用流通,再到个人信息保护边界以及数据作为资产的交付执行等多个核心议题,呼应“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理念,将“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具体化,为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的落地进行有益的司法探索,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参与者提供相对清晰的行为预期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日常使用的各类app,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数据无处不在,其价值也与日俱增。然而,数据权益纠纷也如影随形,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
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的涉数据类案件数量增长明显,2024年一审审结的案件数是2021年的两倍。此外,由于数据具有十分复杂的经济和法律特征,涉数据类案件类型新、审理难度大,裁判结果备受社会关注。
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262—267号),覆盖不正当竞争、个人信息保护、数据产权归属、网络平台账号交付四大核心领域。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
全程参与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评选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此次案例发布覆盖了从数据集合的经营性利益,到企业数据的加工使用流通,再到个人信息保护边界以及数据作为资产的交付执行等多个核心议题,呼应“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理念,将“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具体化,为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的落地进行有益的司法探索,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参与者提供相对清晰的行为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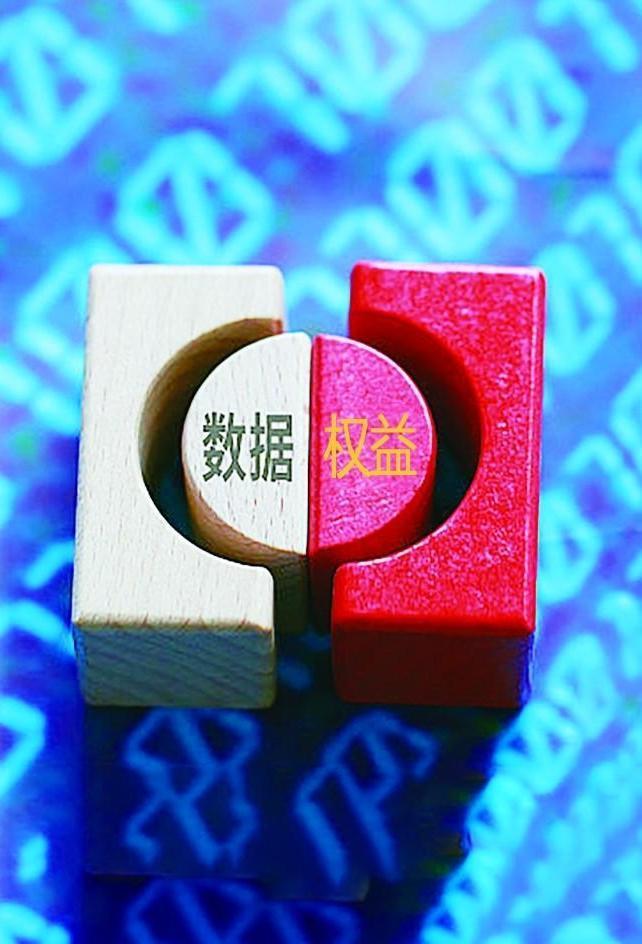
数据竞争的“红线”与“绿线”
数据竞争领域长期存在“数据爬取是否合法”“跨平台数据转移能否允许”等争议,此次发布的262号与263号指导性案例以“一正一反”对照模式,首次为企业数据竞争划定清晰边界。
在262号指导性案例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某文化公司运营的乙app未经许可,抓取、搬运某科技公司甲app内大量短视频、用户信息及评论,导致乙app与甲app内容高度同质化,实质性替代甲app的产品和服务。某科技公司以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某文化公司未经许可,直接抓取搬运甲app中的案涉数据并在乙app展示和传播,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科技公司对汇聚短视频、用户评论、用户信息形成的数据集合享有何种权益;某文化公司获取、使用案涉数据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在甲app中发布的具有独创性的短视频构成作品,但某科技公司并非短视频的制作者,且其对短视频的汇聚仅按常见类别分类,选择和编排无独创性,不构成汇编作品,无法依据著作权法主张权益。然而,案涉数据集合包含短视频、用户注册信息及评论等系某科技公司采集、汇聚而成,某科技公司为数据集合的形成和积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经营吸引大量用户流量,使数据集合产生独立于单一短视频的经济价值,因此其持有、使用、经营该数据集合产生的经营性利益应受法律保护。某文化公司未经许可获取并向公众提供相关数据,足以实质性替代某科技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依法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张凌寒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262号案例为企业数据竞争划定了“红线”,禁止“实质性替代”式的恶意数据爬取。
“该案明确,未经许可将其他平台投入大量资源形成的数据集合进行整体性、规模化地抓取搬运,并用于提供同质化服务,从而实质性替代原平台的核心服务,这种行为因其‘不劳而获’的搭便车属性、对市场竞争秩序的扰乱与破坏以及对网络平台经营者数据集合经营性利益的损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例正是‘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的体现,有助于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红利。”张凌寒说。
与之相对,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某信息公司通过用户授权,实现关联账号间的简历数据转移,法院认定该行为未扰乱市场秩序,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某网络公司运营的甲网站为求职者与招聘企业提供服务,用户可设置简历权限,某信息公司运营的乙网站设有“关联外网账号”功能。某网络公司认为某信息公司通过该功能,让招聘企业用户避开甲网站验证码机制获取、使用简历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诉请停止行为、赔偿500万元并消除影响;某信息公司则称企业用户仅能将简历同步至自身乙网站账号,他人无法搜索。最终,一审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均驳回某网络公司的诉讼请求。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信息公司提供关联账号服务并获取、保存、使用案涉简历数据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网络平台向用户提供关联账号服务,经用户授权后转移其在关联网络平台获取的数据,为用户在合理范围内处理该数据提供便利,未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张凌寒表示:“该案例划定了数据流通的‘绿线’,认可基于‘用户授权’的合规数据转移。这实质上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相关规定的确认和细化,有利于打破‘数据孤岛’,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促进数据要素的合理流动。”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苟博程表示,该案例明确数据流通的合法性,首次认可“用户授权 合理范围”的数据转移行为,为数据要素流动提供司法支持。
苟博程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以往企业在数据竞争中常因“合规边界模糊”陷入困境,而通过正反案例对比,禁止未经许可爬取数据或实质性替代原服务,允许合规数据转移,但需满足用户授权、数据用途正当等条件,引导企业平衡数据竞争与合规义务,避免“数据垄断”倾向。
张凌寒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以往数据权益属性定性模糊,裁判规则也缺乏共识。她进一步解释称:“当处理数据爬取纠纷时,由于数据集合的权益性质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常常只能求助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原则性条款。但何为‘商业道德’,何种竞争行为‘扰乱市场秩序’,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导致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迥异,市场主体缺乏稳定的行为预期。”
“这一正一反的对照传达了所涉纠纷司法裁判的价值取向:保护的是创新性的投入,而非封闭性的垄断;鼓励的是便利用户的流动,而非损人利己的掠夺。这为企业在开展数据业务时提供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即竞争行为是否以损害他人核心经营利益为代价,是否尊重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张凌寒说。
个人信息保护的“必需性”界定
数据权益的诸多场景都建立在对个人信息的合法合规处理之上,个人信息保护是数据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石与前提。但以往司法实践中,“为订立合同所必需”的个人信息收集标准模糊——部分企业以“优化服务”为由过度索权,用户维权时因“举证难、标准不统一”陷入被动。此次发布的265号、266号指导性案例,通过场景化裁判,细化“必需性”标准,解决了这一长期痛点。
265号指导性案例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聚焦“非必要信息强制收集”问题。
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某英语学习网站及app未征得罗某同意,通过线下合作体验店收集罗某手机号码,为其创建网站账号密码,并向罗某手机推送多条信息。为了解账号情况,罗某登录账号后即出现若干问答界面,这些界面要求填写职业、学习目的、学龄阶段、中英文名等必填内容才能完成注册。上述过程中并无“跳过”“拒绝”等选项,亦无授权同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提示。罗某以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该app基本功能服务为提供在线课程视频流和相关图文、视频等信息,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并非其基本功能服务所必需。网站或软件登录注册界面未向用户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登录方式的,属于用户非自愿同意提供个人信息。某科技公司在不具有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事由情况下,未经同意收集罗某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侵害罗某个人信息权益。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令某科技公司向罗某提供个人信息副本、停止处理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书面赔礼道歉及赔偿2900元,某科技公司上诉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凌寒指出,该案的要点在于规制“非必要”的用户画像信息收集。案涉学习app的基本功能是在线学习,但其却强制要求用户提供职业、学龄等个人信息才能登录使用,且不提供跳过或拒绝的选项。这些用于用户画像、精准营销的信息并非提供核心服务所“必需”,这种“一揽子授权”和强制同意的做法侵害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
266号指导性案例则是针对“必要信息的合法收集”。
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2021年3月15日,黄某欢发现自己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开通某信用账户,经询问账户运营商某信用公司客服得知,该账户系其3月7日通过某应用开通重庆公共交通乘车码并使用“先享后付”功能时所开,开通时需点击“同意协议并开通”,下方还用蓝色字体提示可查看相关协议,协议中载明了授权获取个人信息用于实名领卡、授权查询信用分进行风险评估以及某信用公司收集处理用户信息的范围等内容,黄某欢随后要求某信用公司关闭账户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后续账户被注销、信息被删除。3月25日,黄某欢在该应用开通广东省清远市电子公交卡,查阅到相关服务协议(与开通重庆公共交通乘车码的协议内容大致相同),4月25日其自行注销某信用账户。10月13日,黄某欢以个人信息保护纠纷起诉某信用公司,主张该公司在其开通乘车码、“先享后付”服务时存在误导、强迫、非必要开通信用服务的行为,请求法院判令某信用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害。最终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22年4月6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黄某欢的诉讼请求,且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某信用公司在“先享后付”服务中,收集用户信用信息用于风险评估,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为订立合同所必需”,因信用评估是该商业模式的核心环节,且平台已尽告知义务、遵循最小化原则,且收集案涉个人信息不存在误导、强迫等情形。
张凌寒分析,该案例清晰界定“必需性”的场景化标准。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清晰界定了“为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这一法定例外情形的适用边界,避免了“必要性原则”滥用,实现了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场景的平衡。
苟博程提到,以往处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时,“必需性如何判断”是最大难点,而这两个案例提供了可直接参照的裁判标尺,如“教育培训app无需收集信用信息”“信用服务需收集信用信息”,让企业合规与用户维权均有章可循。
原始数据与数据产品的权属厘清
苟博程告诉记者,在实践中,企业数据产品如价格指数、数据库的权属争议突出,数据生产链条复杂,收集者、加工者、平台多方主体对数据权益主张冲突,司法实践中难以明确归属。
264号指导性案例首次在司法层面清晰划分原始数据与数据产品的权益边界,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
某钢铁有限公司诉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某电子公司通过公众号、微信群中以采集、电话询问、销售合同披露等方式,采集钢材生产企业、贸易商的价格信息,经算法加工并按符合“上海标准”的编制准则形成价格指数(非原始价格,反映区域市场综合平均价格),以会员制提供信息服务。
2020年11月,某钢铁公司与某电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某电子公司为其提供数据服务、品牌推广,采集并公布其价格信息;2021年5月起,某钢铁公司以自身价格与同区域同档次企业差异大为由要求下架数据,双方于2021年11月解除协议,但某电子公司仍继续公布相关数据。某钢铁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某电子公司未经同意擅自采集、加工或者编造数据,采集、加工过程不规范、不公允,以此形成并发布的数据不真实,侵害其合法权益。诉请判令某电子公司删除网站及app中所有关于其的信息。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电子公司采集发布案涉数据的行为,是否侵害某钢铁公司的合法权益。
法院认定,双方分别享有不同权益:钢铁公司对原始数据享有权益,而电商公司对合法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享有经营性利益。某电子公司采集加工数据行为不存在侵害某钢铁公司数据权益的情形,且根据在案证据无法认定数据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最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驳回某钢铁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钢铁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凌寒称,此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该案例直接呼应了“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理念,充分保障了数据处理者使用数据和获得收益的权利。
“这是司法层面首次清晰地对原始企业数据与经加工后形成的数据产品进行权益划分,明确了数据处理者对合法采集、经符合有关标准的编制方法加工形成、未对企业权益造成损害的数据产品享有经营性利益。”张凌寒说。
责编:戴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