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现状与检察监督应对
2025-06-26 09:35:04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 新时代刑事执行
■栏目主持人 时延安 仇飞 投稿邮箱:fzzmhlw@legaldaily.com.cn
当前实践中存在评估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结论不明确等问题,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难以充分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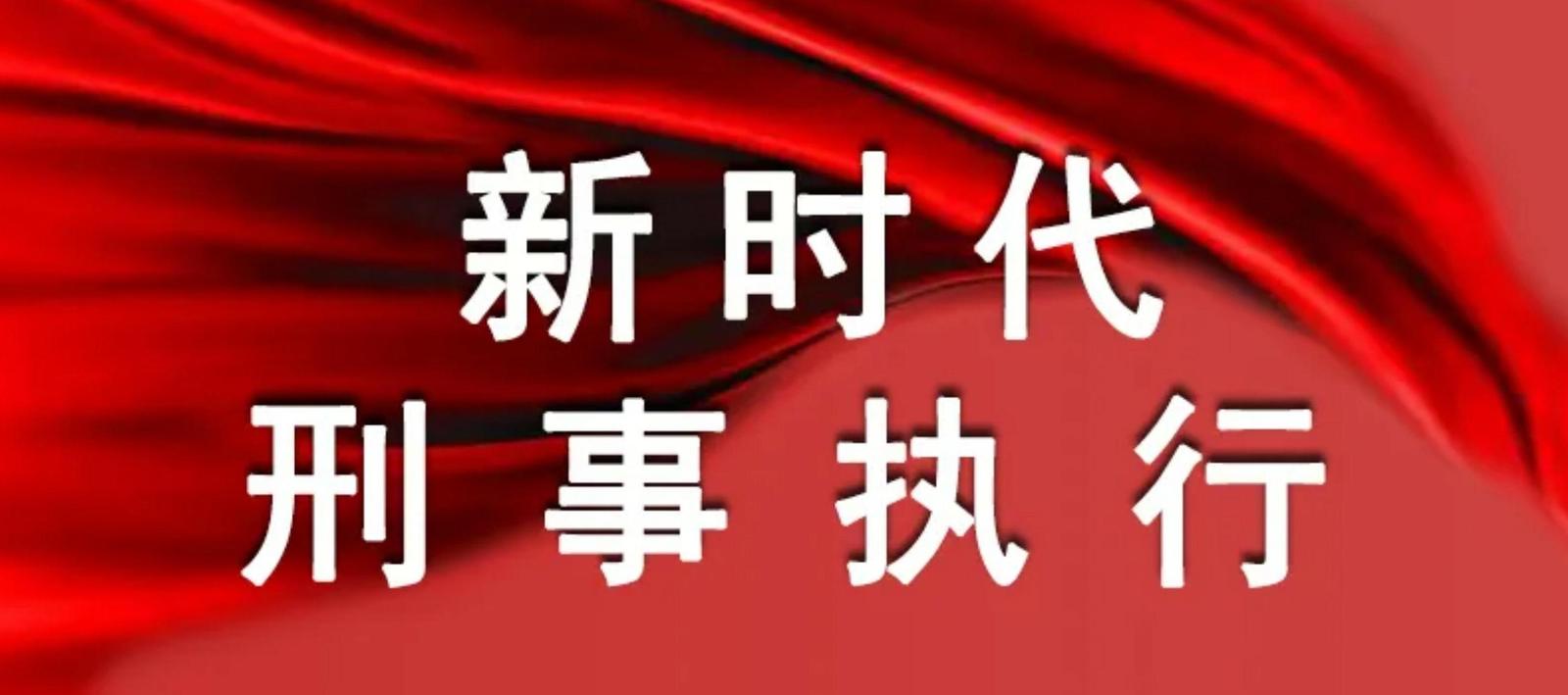
□杨松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近年来轻微犯罪数量不断增加,近五年判处三年(含)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始终保持在82%以上。上述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拟适用缓刑时,需社区矫正机构评估。然而,当前实践中存在评估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结论不明确等问题,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难以充分实现。基于此,笔者结合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困境,探讨检察监督职能嵌入促进轻罪评估法治化、规范化路径。
轻罪案件适用缓刑的社区矫正评估现状与实践需求
当前,社区矫正评估工作正面临轻罪案件数量激增带来的治理压力与挑战。一方面,轻罪案件占比攀升导致治理问题凸显,刑罚执行亦从监禁刑向缓刑等非监禁刑转变,追求“关的少、效果好”目标。而非监禁刑适用需要社区矫正评估,案件上升与治理带来挑战已延伸至社区矫正评估阶段。
另一方面,新型疑难案件导致社区矫正评估危险性难以把握。随着大数据、ai人工智能用于犯罪,突破地域、时空限制新型网络诈骗、网上开设赌场等犯罪呈现,社区矫正机构缺乏有效机制与经验评判,导致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不易评判。
同时,跨时空与城镇化加速社区矫正评估难度。信息技术用于犯罪导致“犯罪地”界线模糊,被评估对象呈“跨区域”状态,“属地”评估难度增加。城镇化背景下,社区基层组织对被评估者社会危险性不掌握,成为社区矫正机构作出不符合矫正条件评估意见依据。
此外,社区矫正评估标准疏漏且不统一。社区矫正评估包括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影响,司法机关调查后尚难以判断,让矫正机构快速判断社会危险性更是考验。
社区矫正评估意见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轻罪案件因认罪认罚获得从宽,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比例上升。社区矫正评估促进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对改变监禁刑为主刑罚执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需要社区矫正评估意见为基础。对认罪认罚被告人拟提出缓刑建议时,一般应当委托评估,减少不经评估即剥夺其非监禁刑资格,有利于促进悔罪,降低冤错概率。
社区矫正评估对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完善刑罚执行制度至关重要。社区矫正制度促进了非监禁刑比例,让被告人在不脱离社会和家庭前提下服刑,同时减少新问题衍生及案件上行,从而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内涵。
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问题与检察监督困境
当前,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尚存在一些问题,检察监督亦面临困境。
一是社区矫正评估法制体系不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源于上海市,2002年,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治工作试点的意见》开创了社区矫正先河。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为社区矫正明确依据,弥补了“刚性”不足缺憾。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丰富了社区矫正对象适用范围,明确了社区矫正机构。2020年7月1日,社区矫正法的实施标志着该项工作步入法治化阶段。
2012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公检法及监狱均可委托调查评估。2019年《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赋予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提出缓刑或者管制量刑建议委托调查或自行评估选择权。而社区矫正法将上述权利限定于社区矫正决定机关,职能调整一度让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缓刑建议陷入困境。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在侦查机关未委托调查评估而检察机关拟提出管制、缓刑量刑建议的,一般应当委托评估,必要时可自行调查评估。
二是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必要性及主体选择不明确。其一,轻罪类型划分与社区矫正评估必要性审查不同步。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范围以危险驾驶、帮信、盗窃等占主要部分,适用缓刑是否均有必要开展评估并不明确。其二,社区矫正评估主体选择不规范。社区矫正法规定系社区矫正决定机关,但又赋予了检察机关认罪认罚案件委托评估权。实践中以社区矫正机构评估为主导,其他有关组织补充作用甚微,检察机关有限自行评估权开展滞后。其三,社区矫正评估救济程序缺乏。社区矫正出具评估意见后即有效力,缺乏救济程序。比如,符合缓刑条件的被告人因调查不全面而被否定评估,被告人缺乏申诉渠道。
三是社区矫正评估机制不健全。首先,社区矫正评估机构界定不清。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以及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应确定的执行地是社区矫正机构,由于评估对象工作、生活等因素流动性致使界定不清,委托有关社会组织进行评估近乎处于空白状态。其次,社区矫正评估力量与专业化不足,严重制约评估工作的全面性、准确性与合法性。社区矫正工作者配备不足、长期兼职,调查评估质量难以保证。家庭、社区等参与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合力未形成。再次,程序与标准不明确导致评估形式化。未明确性侵、涉毒等禁止适用社区矫正案件范围及应当评估的案件类型。社区矫正主观裁量权过于宽泛,评估意见因人而异,且评估内容需要的材料支撑无明确规定,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危险性与对居住社区影响。
四是社区矫正评估监督职能未落实。一方面,社区矫正评估检察监督缺位。因调查评估不充分、规避责任等因素导致评估意见不明确,其原因在于评估机构主动履职不充分,同时检察监督意识不强、监督能力不足,法律监督依据过于原则,导致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目的落空。另一方面,社区矫正评估意见实质性评判不足。检察机关对评估意见实质审查监督乏力、流于形式问题突出。在司法责任制约束下,对评估意见的不当否定面临责任追究,且评估过程监督处于空白状态,而评估意见系调查后作出,监督纠正必须具备充分的法律与事实依据。
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的检察监督路径优化
笔者认为,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的检察监督路径优化,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凝聚社区矫正评估工作合力。首先,提高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评估深度。对危险驾驶、轻伤害等提出缓刑建议时一般不再评估,实现繁简分流。对需要委托评估案件,应移送涉案事实、情节及影响评估意见的材料。同时,应强化对评估过程、参与主体的检察监督,提升评估准确性。其次,强化社区矫正机构履职能力与接受监督自觉性。评估意见是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依据,涉及当事人利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治理成效,矫正机构要提升履职自觉、主动接受监督,促进评估意见合法、准确、规范。再次,加强评估意见实质性审查。作为适用非监禁刑重要参考,评估意见必须明确。司法机关应当对其出具依据、调查全面性、意见客观性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采信。
二是完善社区矫正评估法律体系。以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适用条件以及第七十四条缓刑禁止性条件为原则,在社区矫正法层面统一委托主体、评估规范,细化矫正机构确定规则,强化检察监督权。由检察机关根据涉案罪名、在案证据、认罪悔罪态度等裁量是否需要评估,赋予检察机关委托与自行评估选择权。
三是构建轻罪案件社区矫正评估机制。其一,明确调查评估前置条件。建议结合案件罪名及犯罪情节划分应当委托、裁量委托及无需委托类别,如危险驾驶案一般不需评估,而多次盗窃拟适用缓刑应当委托评估。评估主体由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必要时由犯罪地、户籍地矫正机构协助。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评估难度不大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对于一般案件3个工作日完成,情节复杂不超过7天,特殊情形评估意见应当在委托机关作出决定前反馈。其二,制定评估清单,明确参与主体职责。建议以盗窃、帮信等类案为基础,制定调查清单,探索将人工智能引入社区矫正评估以规范意见出具过程,限制裁量空间。明确矫正机构对家庭、社区等参与主体引导责任,规范意见提供程序、内容及形式,避免材料失真。其三,建立评估协作与反馈机制。建立评估过程协作会商机制,交换意见、补充材料,促进评估意见准确性,对新型疑难案件将听证意见作为参考。建立评估意见双向说理机制,评估意见具有正当性与法律效力,采纳为原则,如不予采纳应予以说明。建立评估意见申诉机制。鉴于评估意见对当事人影响重大,有必要建立评估意见申诉机制,必要时邀请第三方参与论证、监督。
四是完善社区矫正评估检察监督与自行评估制度。首先,前置社区矫正评估的检察监督阶段。检察机关委托评估至评估意见反馈期间监督处于空白,检察监督仍以事后监督模式为主。笔者建议将监督节点前移至社区矫正评估过程,填补评估阶段监督空白缺陷。其次,将社区矫正参与主体纳入检察监督范围。参与主体意见对评估结论有重大影响,通过审查其提供材料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监督。强化法院不采纳评估意见的监督权,减少裁判随意性。当出现和解等可能适用缓刑时,可建议法院委托评估以保障被告人获得非监禁刑机会。再次,探索检察机关自行评估机制。检察机关必要时自行调查评估判断过于宽泛,建议赋予检察机关选择自行评估或委托评估裁量权,取消顺序限制。在自行评估环节中,保证至少有一名检察官参与,可通过公开听证、邀请社区组织、家庭成员,提升公开性与公信力,让符合非监禁刑条件被告人以“不脱离”社会方式接受矫治。
(作者系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编: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