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pk“验资局”中的法律风险
2025-07-10 16:10:34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宝子们验资啦,不要被追上啦。”“晚上这么久没见,让我看看兄弟们的底蕴吧,不会还不如下午吧。”“家人们,一人只要一颗小心心、棒棒糖。”“不争馒头争口气,先破10万。”……
4到5名主播坐在屏幕前,通过各种话术或手势不断动员粉丝们刷礼物打赏,以收到礼物的数量是否达标或分值多少来决定主播pk的输赢。
近日,“多名主播验资pk引争议”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关注。尽管随后平台要求相关涉事主播停播,但关于“验资pk”现象的争议并未停息。有网友认为该行为诱导非理性消费,还助长了社会攀比风气;也有网友认为打赏并不违法,而且平台允许或默许这些灰色玩法。
那么,粉丝的打赏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何种性质?“验资pk”涉及哪些法律风险,又该如何治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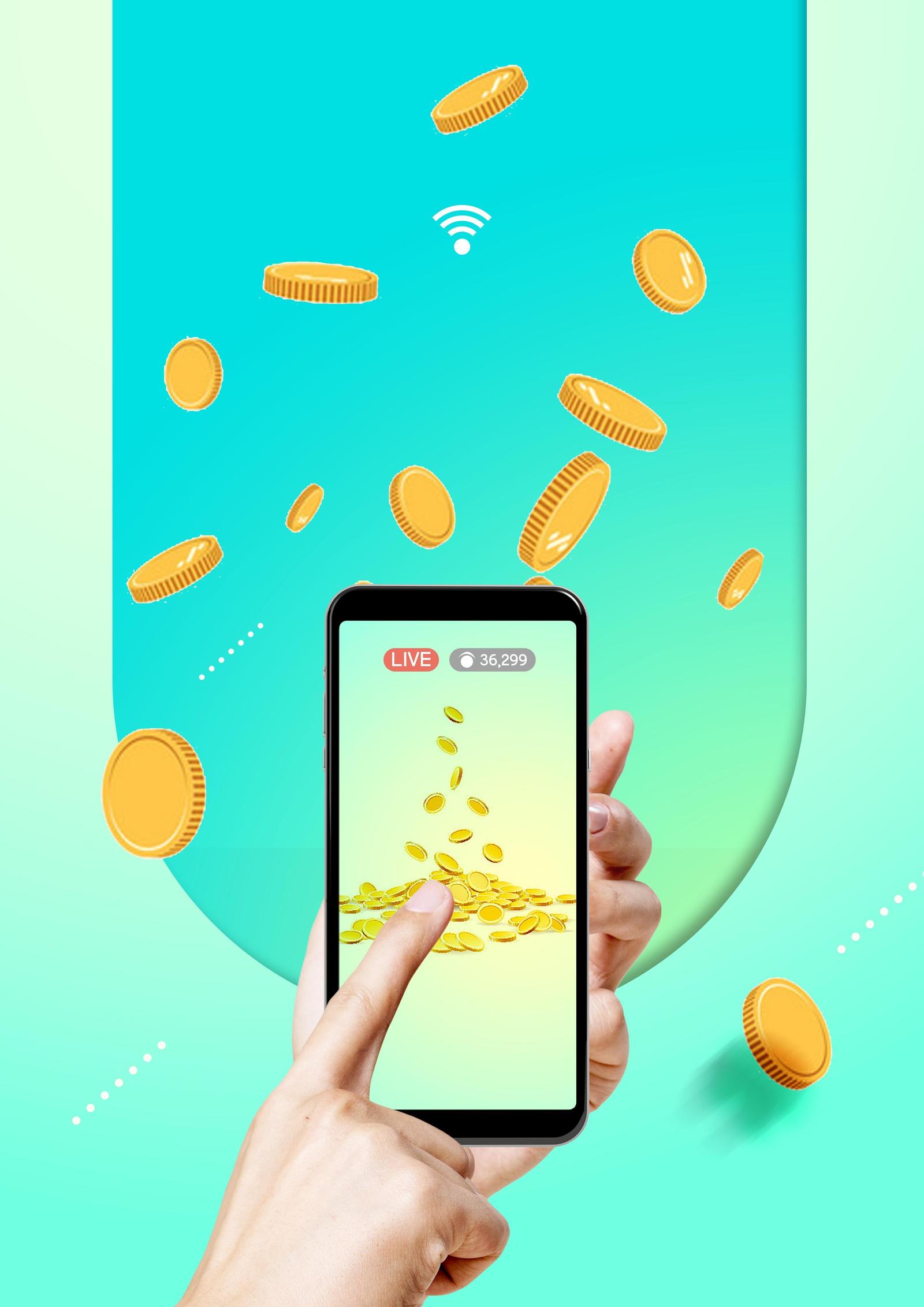
视觉中国供图
多名主播“验资pk”流水超千万元
6月28日晚,某平台主播孙恩盛、皮皮皮皮朱、三斤、陈俏俏等主播,联手开启了一场“验资pk”直播马拉松。
除陈俏俏粉丝数为50余万外,其余3名主播粉丝数均超400万,其中,孙恩盛粉丝数更超770万。当晚,以这4人为主的多名主播连续进行了12轮至14轮“验资pk”,每轮要求粉丝在60秒内刷礼物达到“100万分(点)值”。未达标主播接受惩罚,如表演才艺等,全员达标则进入下一轮。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上述平台规则发现,连屏期间观众送1钻石礼物相当于1点值,虽然还可以通过观众点30赞获取1点值,但每10分钟内通过点赞观众最多贡献5点值,且每位主播最多通过点赞获得5000点值,在主播们100万的目标中点赞分值可以忽略不计。
1元可以充值10钻,这意味着,100万分值约为10万元人民币。多名观看了这场pk直播的网友回忆,平台送礼数值最高只显示“100万 ”,而多名主播几乎每轮都打满了100万分值,当晚总打赏流水估值1200万至1400万元,扣除平台约50%的抽成后,参与“验资pk”的主播税后收入均超百万元。
“一般‘验资’一到两轮,没见过一下子14轮的,所以舆论才这么大。”上海市的张若(化名)今年5月第一次观看了所谓的直播“验资局”。她回忆,当晚三女一男4名主播轮流喊“验资”“刷礼物”,每人都获得了“100万 ”分值的礼物。
那时,张若才知道,所谓“验资”,不是验主播的资,而是粉丝的资,其检验的是主播粉丝的含“金”量。而据多名长期关注直播“pk”圈的网友反映,“验资局”或“验资”游戏不是最近才兴起的现象。仅以某平台为例,去年就有超千万粉丝的主播倪海杉开创“pk验资局”。“‘验资pk’或‘pk验资’都是pk形式的一种变种”。虽然叫法不一,但单纯以粉丝刷礼物的实力来决定主播pk输赢的玩法一直存在,从早期虎牙的“神豪大战”,到现在短视频平台的“验资”。
记者调查发现,与“验资pk”类似的还有“pk验资”或“pk门票”,即主播若要参与与其他主播的直播pk,尤其是与头部主播的pk时,先要进行“验资”。只有粉丝打赏达到一定金额才能参与pk,或给头部主播送礼物达到一定金额才能参与pk。
“我们是玩一轮(验资)就打pk了,他们pk都不想打了,就不断验资。我建议老东家(平台)直接把pk板块收了。”倪海杉于去年8月被某平台永久封禁后转战其他平台,在这场多人“验资pk”引发争议后,他评论道。
粉丝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存争议
“宝贝们,我休息一下哦。”6月30日,孙恩盛向粉丝表示暂时停播。随后,多家媒体也证实,平台于当天要求上述“验资pk”涉事主播停播。
记者调查发现,截至7月8日,孙恩盛、皮皮皮皮朱、三斤、陈俏俏于6月29日后均未在某平台直播;再在另一平台上,经常进行“pk验资”和“pk门票”玩法、粉丝超3300万的头部主播刘二狗,6月29日后也未进行直播。
然而头部主播的停播,并未使“验资”游戏停止。7月8日,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验资局”,但记者在不同直播平台上,仍看到有“pk主播”在进行通过直接送礼达标与否来定pk输赢的现象。在一场3名主播的pk中,其中一轮的送礼目标依次为“15颗棒棒糖(9钻)、5个墨镜(99钻)、3个礼花筒(199钻)、2个比心兔兔(299钻)、1000个小心心(1钻)”,礼物目标金额逐渐上升。
无论是“验资pk”还是“pk验资”,其“验资”过程实质都是粉丝打赏。而对于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律界人士表示存在争议。
“关于打赏行为的性质,在学术研究、监管及司法实践中,曾经有‘赠与合同说’‘服务合同说’两种争议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从直播打赏行为的商业本质、主播与平台的经营特征、打赏用户的互动行为及获得的精神文化价值等方面综合看,打赏行为属于用户与主播间、用户与平台间的新型网络服务消费,各方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验资pk’仍然是主播、用户之间通过直播口播、实施打赏行为等方式所形成的网络服务合同及其履约过程。”刘晓春指出,关于服务合同这一观点在相关监管规定、司法实践中也获得普遍认可。例如,2021年2月,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0条规定,“建立直播打赏服务管理规则,明确平台向用户提供的打赏服务为信息和娱乐的消费服务”。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告诉记者,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在实践中主要有赠与合同和服务合同两种观点。若粉丝打赏时未附加任何条件,单纯是对主播的喜爱与支持,该行为更倾向于赠与合同,即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另一方,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关系。然而,如果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承诺了特定的互动、表演或服务作为粉丝打赏的对价,那么,此时打赏行为可能构成服务合同关系,粉丝支付金钱以换取主播提供的相应服务。
主播话术可能涉及诱导非理性打赏
事实上,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直播平台的打赏消费早有相关治理要求。
2020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在用户每日或每月累计“打赏”达到限额一半时,平台应有消费提醒,经短信验证等方式确认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消费,达到“打赏”每日或每月限额,应暂停相关用户的“打赏”功能。平台应对“打赏”设置延时到账期,如主播出现违法行为,平台应将“打赏”返还用户。平台不得采取鼓励用户非理性“打赏”的运营策略。
“《通知》首次提出,平台应对直播打赏限额,但没有制定具体行业标准或落地细则。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个体消费能力的不同,难以制定具体统一标准,对直播打赏消费的金额、范围进行限制客观上难以实施;且平台单方限制,也可能违背用户作为消费者的消费自主权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自治与行为自由。”刘晓春表示,因此,《意见》对《通知》的要求进行了细化,规定应当对单个虚拟消费品、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对单日打赏额度累计触发相应阈值的用户进行消费提醒,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和延时到账期。当前,行业内头部直播平台已落实该意见的倡导,设置了多重消费提醒,引导用户理性消费。
但马丽红指出,目前,我国对于打赏的具体金额上限,并没有全国统一明确的具体数字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平台的执行带来了操作空间。
尽管上述部门规范性文件中对防范非理性打赏提出了相关要求,但在“验资pk中”,主播们会通过各种话术动员粉丝打赏,如“每一次刷礼物都是对主播的爱”“家庭凝聚力的体现”“可以输但不能认输”等。那么,主播的行为是否涉及诱导非理性消费?
刘晓春指出,“验资pk”过程中,主播可能以不当话术等方式,诱导、胁迫或刺激用户打赏,涉嫌诱导用户非理性消费。这种情况下,主播涉嫌违反《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第十四条中的相关规定,应承担相应后果。
“这种竞争性的‘验资’活动可以说是饭圈文化的一种表现。从‘验资pk’的过程来看,主播通过各种话术动员粉丝打赏,这种行为有较大可能涉及诱导高额打赏和非理性消费。”马丽红分析,主播利用情感因素,将打赏与情感表达、群体归属感以及竞争心理相挂钩,使粉丝尤其是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以及缺乏较强自制力的成年人,在情绪冲动下进行大额打赏,而未充分理性地考虑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消费能力。在“验资pk”的紧张氛围下,一些粉丝为了维护所在主播的“面子”或在群体中获得认可,可能会超出自身经济能力进行打赏。这种诱导行为不仅可能导致粉丝个人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不良的社会风气,如盲目攀比、过度消费等。
刘晓春直言,如果有未成年人用户(通过使用成年人账号等方式)参与打赏,该行为可能构成无效或可撤销法律行为,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求退款时,主播和平台应当承担相应退款责任。
“验资pk”可能涉及其他法律风险
除了可能涉及诱导非理性消费、未成年人打赏、社会盲目攀比等以外,专业人士表示,“验资pk”还可能存在其他法律风险。
刘晓春举例,如果“验资pk”过程中存在主播与用户串通,通过直播打赏转移赃款等违法所得的,则视具体情况主播可能与打赏用户构成共同犯罪或构成帮助犯罪;平台在“明知”主播与用户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仍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马丽红指出,从平台责任方面来讲,若平台未按照规定对用户打赏金额进行限制,纵容大额打赏行为,则违反《规范》,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如警告、罚款、暂停相关业务直至吊销相关许可证等。从主播责任方面来讲,如果主播在直播中存在欺诈行为,如虚假承诺表演却未兑现等,可能需依据民法典承担违约责任,向粉丝返还打赏款项。粉丝方面,若成年粉丝是使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高额打赏,在司法实践中,若该行为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未获得配偶同意,配偶一方可通过起诉确认打赏无效并追回款项,但需举证证明该资金用途与家庭生活无关。此外,若存在利用打赏进行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则将面临刑事法律责任追究的后果。
“我不认可‘验资pk’行为,可以道德批判、可以舆论引导,但只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对此进行限制,法无禁止即可为,就不能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涉。当然,如果涉及未成年人打赏、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等,则可以通过民法典等法律规定进行追责。”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坦言,尽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对打赏行为有相关规定,但禁止“验资pk”行为本身于法无据。此外,平台可以依据相关规范进行治理,但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形下,平台治理效果有限。
“从此次‘验资pk’事件可以看出,平台监管存在一定缺失。”马丽红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平台算法机制助推高额打赏直播间流量,使得这类存在争议的直播模式得以迅速传播和放大影响,这反映出平台在流量分配和内容导向方面缺乏合理的把控。另一方面,平台长期默许“验资pk”等灰色玩法,对主播的行为规范监督不力,未能及时制止这类可能诱导非理性消费、违背公序良俗的直播行为。
直播“验资”需多方协同治理
“这类现象不仅容易引发非理性消费、破坏健康的直播生态,还可能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容易传递错误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引发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马丽红直言,对于直播中的各种“验资”现象,应当进行治理。
平台方面,马丽红认为,应通过完善规则与技术防控、强化身份核验与未成年人保护、优化算法推荐机制等三方面进行改进。如建立健全针对直播内容和打赏行为的详细规则,明确禁止各类诱导打赏、非理性消费以及违背公序良俗的直播行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时监测直播间的打赏金额、主播话术以及用户消费行为等数据;采用人脸识别、与公安系统数据对接等多种方式,确保未成年人无法进行大额打赏;调整算法规则,不再单纯以打赏金额、流量等作为主要的推荐指标,而是增加内容质量、价值观导向等因素的权重等。
平台治理以外,马丽红还建议,加强立法与执法、加强行业自律与规范完善、提升公众意识与教育。例如,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针对网络直播行业的法律法规,明确“验资”等各类直播行为的法律边界,细化对诱导打赏、违规直播等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定期对直播平台和主播进行检查,对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形成有效的法律威慑;推动直播行业建立自律组织,制定行业内部的自律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通过媒体宣传、公益广告、学校教育等多种途径,提升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直播打赏的理性认识,增强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等。
刘晓春建议:“一方面需要主播群体自觉遵守《规范》,摒弃不当或违规直播行为;打赏用户理性表达、合理消费,不参与或营造不良互动氛围。另一方面,平台也需不断基于违规行为新形态,丰富审核标准提升风险识别能力,积极阻止不良信息传播;对平台发现的诱导消费违规行为进行严格处罚。”
在刘晓春看来,整体而言,直播内容存在参与主体众多、衍生玩法不断新增的特点,其实时性特征决定了仅依赖平台前置识别风险存在客观限制,平台在尽到及时处罚、在技术可行范围优化提升审核能力等义务情况下,应视为其履行了相应管理义务,不应再承担法律责任。对违规打赏行为的治理,也需要平台、主播、用户等多方协同,方能构建健康、理性的直播打赏生态,维护用户权益与网络秩序。
责编: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