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想象与法律经济学的前提
——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2025-09-12 09:54:01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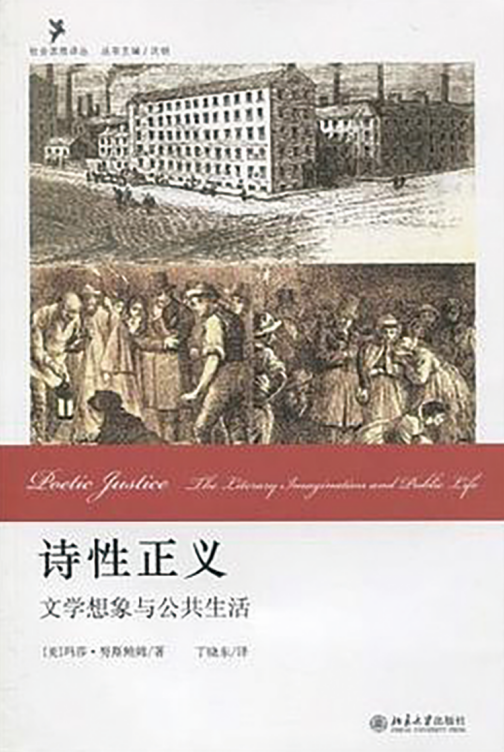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作者:[美]玛莎·努斯鲍姆
译者:丁晓东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想象的情感应当超越旁观者的视角,在读者与对象之间建构更为血肉的紧密联系。而且,文学想象所建构的情感也不应止步于努斯鲍姆所说的爱与同情,更不应当滑入短暂同情与自我感动的陷阱
□丁晓东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的作者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与哲学系的双聘教授,古希腊与罗马哲学、法律与伦理等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本书则是一本写给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同时也是批判波斯纳以及波斯纳所主张的法律经济学的书籍。在本书中,努斯鲍姆认为,那种粗糙版本的法律经济学无法为正义或司法(英文都是justice)提供正确的指引。作为替代,努斯鲍姆在本书中提出以文学想象与具有共情能力的中立旁观者作为指引,为正义与司法提供新的基础。
本书对于法律经济学的批判与对于文学想象的呼唤,为我们反思法律经济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法律经济学可以提供对很多问题的洞见,但却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存在盲点:法律经济学分析与实施本身依赖于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而文学想象是构成共同体建构与维系的重要纽带。但另一方面,努斯鲍姆在本书中所诉诸的文学想象与情感建构也远远不够。文学想象与情感建构应当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其所建立的并非旁观者与被观察者的同情关系,而是具有血肉联系与责任伦理的政治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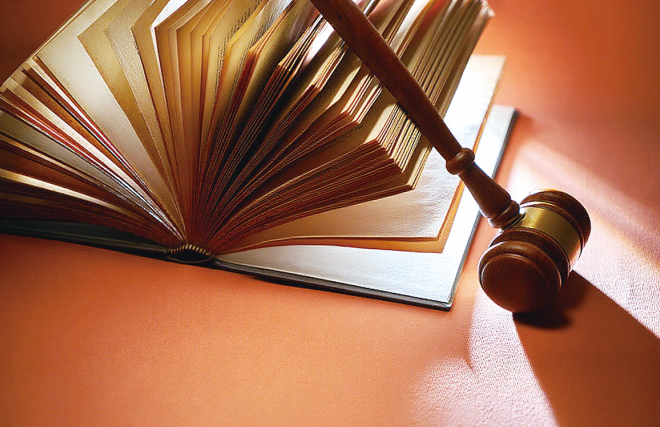
法律经济学的前提
本书的批判对象是法律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本书之前,此类批评已经汗牛充栋。有理论认为,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无法成立;其他理论认为,法律经济学所追求的财富最大化或效率最大化不具有正当性;还有理论认为,法律经济学忽略了财富差距、社会地位差异等公平问题。本书在呼应这些批评的同时,引入了文学理论与情感哲学层面的批判。努斯鲍姆指出,那种粗糙版本的经济学将人简化为物,不仅在事实描述层面不同于每个人的丰富世界,而且在规范层面无法真正促进社会福利、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相反,通过文学畅想可以更为整全性地认识世界,同时提供更为中立和关注弱势群体的司法裁判。
在美国学界,法律经济学对于批评意见也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应与反驳。就理性人假设而言,有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对传统理性人假设进行了部分修正,例如,行为主义法律经济学引入了有限理性的理念。其他法律经济学理论则指出,理性人的假设只要整体上有利于问题分析即可,并不需要与实际完全符合,就像在多数情形下,假设地球是平的并不妨碍人们对各类问题的分析。就社会福利与不平等问题而言,有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则主张,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公平问题应当交由立法机关实现。法院或司法机关在没有明确立法规定或存在争议的情形中,则应以法律经济学作为指引。一旦对照反驳意见,文学想象对于法律经济学的传统批评就会大打折扣。即使是努斯鲍姆自己,也一再承认其反对的并非经济学本身,而是那种“粗糙版本”的经济学。
但如此一来,本书所要辩护与提倡的文学想象与情感分析的必要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在经济学的强势攻击下没有立足之地。要反驳与回应经济学的主张,需要回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法律经济学存在的前提是什么?法律经济学要能够进行分析与应用,其前提是存在一个可以应用法律经济学的政治共同体。如果政治共同体不存在,那么法律经济学的分析与应用就会演变为拙劣的争权夺利与利益算计,与法律经济学所追求的共同体财富最大化或效率最大化背道而驰。
当然,法律经济学或经济学很少思考政治共同体问题。因为在法律经济学看来,共同体的建构是政治问题或革命问题。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已经建立了政治共同体与法院等国家机构,已经为法律经济学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政治共同体并未完成建构的国家或地区,法律经济学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这并不是法律经济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法律经济学将自身定位为“管家”角色。“管家”并不需要考虑家庭的建立与情感维护,“管家”最主要的角色是对家庭收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维护家庭财富最大化。
法律经济学如果能够严守其自身有限的“管家”角色,问题当然不会太大。不过法律经济学的雄心显然不仅限于对纯粹经济问题的分析。从公共选择理论到家庭关系分析,法律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是没有边界的:万物皆可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定位也从来不是共同体建构下的分析工具,其本身总是蠢蠢欲动,试图将“管家”思维应用于整个家庭或共同体。本书所分析的《艰难时世》中的主角葛擂硬,可谓是此类思维和后果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家之主的葛擂硬信奉经济学的前身功利主义哲学,处处以此种哲学教育与要求其子女。结果,其女儿被迫嫁给虚伪资本家,婚后精神备受折磨;其儿子嗜赌成性,最终堕落为盗贼。家庭作为自然形成的紧密共同体,其纽带尚且会被纯粹功利主义的思维所侵蚀。作为规模更为庞大、关系更为松散的政治共同体,如果仅以功利主义或各类经济学的思维对其进行建构与维系,就更加容易成为一盘散沙。而共同体一旦溃败,那么法律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文学想象与共同体建构
从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出发,文学想象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文学想象的价值在于,其能够建立人类的意义与价值体系,使得人类可以超越基于纯粹生物性的共同体建构。在自然世界中,动物可能凭借其本能而形成家庭、部落等共同体,但不可能存在各类组织、社群、阶级、民族、国家、帝国、天下等人为建构的共同体。古希腊哲学曾经以自然与人为习俗作为思考的起点。但从更本质的层面看,人类社会恰巧是人为建构的,人为建构与想象构成了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社会或自然界的最本质区别。
文学想象与共同体建构的命题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直是核心议题。在西方,柏拉图虽然在终极意义上站在哲学一边反对诗歌与文学,但其所设想与建构的次优共同体离不开神话叙事与意义建构。卢梭则是对共同体建构思考最为深刻的现代思想家之一,卢梭认识到,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的建构不能基于纯粹的功利主义与利益叠加,而是需要通过公意建构与公民宗教进行维系。在中国,儒家经典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本身就是一种对不同共同体的想象,这一想象后来也被费孝通先生归纳为经典的差序格局。及至近现代,儒家的共同体想象又被认为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格格不入。中国当代革命发源于新文化运动,也并非偶然,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对于新政治秩序与共同体的重新想象。
但在当代学术分工体系下,有关文学想象与共同体建构的讨论日渐稀缺。文学被纳入文化艺术研究的范畴,其共同体建构的功能并未获得太多重视。倒是在一些跨学科研究与思想类畅销书著作中,这一议题不断引起思想界与社会的关注。例如,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指出民族国家的建构依赖于报纸、媒体等文学所引发的共同体想象。在近年来的畅销书著作《人类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也讨论了对虚构事物的想象能力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正是这种能力使得由陌生人所构成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从看客视角到共同体视角
在本书中,努斯鲍姆引用不同文学作品,论述了文学想象在超越功利主义、建构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本书集中论述了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通过这部小说揭示了粗糙版本的功利主义对于人类情感的异化。本书也提到了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通过这部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作来揭示美国黑人被非人化对待的现状。本书还提到了惠特曼,通过惠特曼的诗歌,努斯鲍姆呼唤对“被排斥者、被鄙视者”进行关注,“分担被侮辱者受到的侮辱”“给予被排斥者遭受的痛苦、被骚扰者受到的威胁以声音”。
但对于这些小说所建构的情感与共同体,努斯鲍姆又极力地在读者与对象之间进行区隔。努斯鲍姆似乎担心,如果读者与对象之间的情感超越了同情和中立性,则文学想象就可能成为偏私与狭隘性的情感。在努斯鲍姆看来,并非所有的小说和情感都值得信赖;而要区分可信赖和不可信赖的情感,就需要建构一种“明智旁观者”的视角。正如努斯鲍姆所述:明智的旁观者“虽然他作为一个关注的朋友去关心参与者,但他并没有亲自卷入他所目睹的事件。因此,他将不会有涉及他自身安全和快乐的那类情感和想法;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没有偏见的,而且以某种超然来审视他眼前的情景……另一方面,他也不会由于这个原因而缺少感情。在他最为重要的道德能力中,其中一种就是生动想象的力量,想象成为他所想象的那些人中的每一个将会是怎样的”。
旁观者的视角淡化了文学想象对于建构共同体的意义。旁观者的视角看似可以保持读者中立,维持读者与对象的共情,但却可能使这种共情成为一种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责任伦理的关系。这种关系正与惠特曼等人所描绘的情感关系背道而驰。在本书所提到的《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中,惠特曼写道:“人,只有由他们,这些州才能融合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用契约或强制把人民结合在一起是没有意思的/只有那种把一切像身体的四肢或植物的纤维那样聚集在同一生活原则下的力量,才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在惠特曼笔下,文学所产生的情感并非像旁观者那样疏离,而是“像身体的四肢或植物的纤维那样聚集在一起”,有着血肉相连的共同想象。
事实上,旁观者的情感不但过于疏离,而且可能演化为廉价的同情,甚至是令人痛心的冷漠。对于冷漠旁观者的描写,没有哪位作家比鲁迅先生更为形象与深刻。在《药》中,鲁迅先生生动地描写了看客的形象:“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在《祝福》中,当祥林嫂讲述她孩子被狼叼走的悲惨故事,“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之后,当祥林嫂不断重复自己的悲惨故事,“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旁观者角色的麻木冷漠跃然纸上。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努斯鲍姆本人也像鲁迅笔下的那些旁观者那样冷漠麻木。作为一名精通希腊与罗马哲学、现代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的学者,努斯鲍姆本人对于弱势群体有着持久的关注,对“情感”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着特殊的关注。这里只想指出,文学想象的情感应当超越旁观者的视角,在读者与对象之间建构更为血肉的紧密联系。而且,文学想象所建构的情感也不应止步于努斯鲍姆所说的爱与同情,更不应当滑入短暂同情与自我感动的陷阱。在爱与同情之外,面对社会不公的愤怒、面对艰难困苦的隐忍、面对挫折失败的乐观,这些深刻联结共同体的情感都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努斯鲍姆所呼唤的文学想象与情感建构,或许不是太多了,而是太浅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责编: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