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苦难与救赎的藏地传奇
评电影《洛桑的家事》
2025-10-17 10:47:53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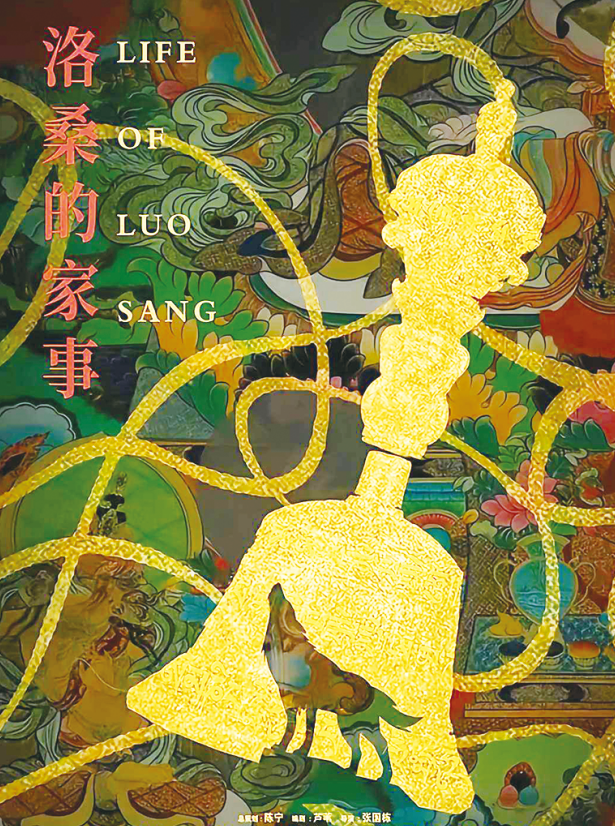
图为电影《洛桑的家事》海报。
□李佳
走进电影《洛桑的家事》,便走进了辽阔而神秘的藏地世界。高原之上,雪山之下,天地无垠,人渺小而清晰。这是一个典型的藏地故事。影片自创作以来,在国内外屡获佳绩:2024年10月,于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得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和最佳女主角两项提名。今年9月11日,其在全国艺联专线影院正式上映。
情、理、法的极限拉扯
影片的主人公们生活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远方是终年不化的雪山,近处有牧场与牛羊。生活虽艰苦,却不乏酒与歌舞的点缀。他们都是平凡人,故事散发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豆拉伽腿部因伤致残,中年潦倒,遭妻子抛弃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且有酗酒习惯。一天,他酒后驾驶拖拉机,不慎撞倒洛桑的孙女央金,导致央金双腿瘫痪。这起事故将三个家庭拖入“深渊”:洛桑一家深陷痛苦与愤懑,洛桑坚持要通过法律途径起诉豆拉伽,誓要让其承担应有的责任。豆拉伽满心悔恨,却无力赔偿,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他的妹妹卓玛作为牧区唯一的医生,也倾尽全力试图补救。然而,悲剧已然酿成,身陷其中的平凡人能否获得救赎?这,便是“洛桑的家事”所讲述的核心命题。
渺小却不卑微,偶然却并非罕见。即便置于藏地,这样的故事放到任何地方,都能孕育出动人的叙事。因此,影片具备扎实的叙事基底。主人公们遭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困境:生活的意外悲剧,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理、法的激烈碰撞。世间悲剧的发生,往往只在一瞬间,但其影响却可能如潮水般蔓延,渗入“骨髓”,将局中人磋磨得形销骨立。这个过程令人揪心,也耐人寻味;而“每个悲剧各有不同”的特质,又让故事能延伸出多种情节走向,通向那谜一般却又无法摆脱的命运,于细微处牵动观者的心绪。
“洛桑的家事”叙事丝丝入扣,引人入胜。最先拨动观众心弦的,是央金的命运。当这个7岁小女孩拖着细弱的双腿在地上艰难爬行时,任谁都会为之动容。她的未来会怎样?她还能重新站起来吗?这些影片未曾直接提出却始终萦绕在观众心头的问题,不断搅动着忧伤的涟漪。正因为这份共情,观者与央金一家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连接,不知不觉间便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洛桑的愤怒难以平息,任谁劝说都不肯原谅豆拉伽,坚持要让肇事者受到惩罚——这份执拗落在观众眼里,完全合乎情理。
但痛苦并非只属于洛桑一家,豆拉伽同样深陷煎熬。心债最难偿还,善良的人往往更容易背负心债;而这个故事最具魅力之处,就在于所有局中人都保有善良的底色。为了偿还这份心债,豆拉伽在拼尽全力,卓玛也在竭力补救。豆拉伽甚至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对可能面临的任何惩罚都毫无怨言。可他尚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他若入狱,孩子们的生活该如何维系?卓玛想站出来承担责任,可自家家境本就拮据,无力额外赔偿,加之她已身怀六甲,丈夫为此与她爆发了激烈冲突。法律层面的正义诉求、人间的情理考量、情感天平的平衡,一时间盘根错节,这个“结”该如何解开?——谁必须作出妥协?谁又要承受牺牲?这样的抉择,对任何人而言都沉重无比。情、理、法的极限拉扯,让叙事张力逐渐拉满。
独特的叙事抵达救赎
这个故事即便用常规方式讲述,也足以出彩。但影片采用了一种更为独特的叙事视角:它不仅讲述人与人、家与家的关系,更深入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联结。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下,个体遭遇的不幸被注入了命运的悲怆感;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法律层面的是非对错,也得到了另一种更具哲思的解答。
影片的对白不多,情感表达克制而深沉。痛苦几乎是“无声”的——小姑娘央金被撞断双腿后,观众从未听到她的哭闹。她每次出场,总是在众人的注视下,在地上努力而艰难地爬行,仿佛在地面上刻出了两道深深的痕迹,这痕迹也成了观众心底无法磨灭的印记。疼痛虽未以激烈的方式呈现,生活却仍在继续,且不乏庆典与仪式的温暖:飘动的五彩经幡下,神圣的白毡房周围,人们笑着唱歌、跳舞,庆典上有酒有肉;洛桑一家也身处其中,未曾因痛苦而隔绝于生活之外。“妈妈,我想跳舞。”突然,小央金轻声说道。那一刻,伤痛是笑着表达的,原来它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苍穹之下,众生平等,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伤痛,成为天地自然的一分子。
寻求解决之道与救赎之路,同样在自然之中展开。为了赔偿洛桑家、凑钱给央金治腿,豆拉伽和卓玛走进了雪山。在山脊之上、寒风凛冽之处,生长着珍贵的虫草。在山外人眼中,虫草“很值钱”;但对豆拉伽而言,挖虫草是他能想到的最直接的赎罪方式。挖虫草的过程异常艰难,辛苦一天往往只能挖到十几根。挖虫草的人沿着山体向上攀爬,弓着身子仔细搜寻,模样如同虔诚的苦行僧。当镜头从他们身上缓缓拉开,将整座雪山纳入画面时,两人的身影渺小得如同两株低矮的植物,在银幕上几乎快要消失;而他们身上的苦难与哀伤,也随之渐渐隐去,消融在皑皑白雪里。
人生无常,自然亦无常;二者相互交融,既为彼此带来变数,也孕育着转机。人与人之间解不开的结,或许自然会给出答案——有时,只需坚守本心,静静等待变化的发生。变数,在一个暴雪天到来:风雪之中,央金的妈妈遇险,彼时她已临近预产期,若不能及时获救,极有可能面临一尸两命的危险。恰巧此时,豆拉伽前来送赔偿款,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央金的妈妈突发早产,又是豆拉伽顶风冒雪将卓玛接到现场……那一刻,无情的风雪成了见证真情的场域;随着新生命的诞生,过往的恩怨也在慢慢冰消雪释。风雪无言,荡涤着一切,也诉说着世间最深邃的妙谛。
与自然对话,与万物共生
所有故事都发生在高原雪山的广袤天地间。电影开篇,悠扬的藏地牧歌响起,将观众的思绪缓缓拉入这片圣洁的土地:树林、草原、溪流,巍峨的山脉,遥远的日轮,美得仿佛不真实,却又似是世界原本该有的模样。这份静谧的美景,许久之后才被人声的喧闹打破;而影片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人出现在自然美景之后,又在自然美景之中。
导演张国栋曾带着主创团队,冒着零下30℃的严寒,在海拔4000米之处实景拍摄。他们的镜头语言呈现出的藏地景象,是生动的、带着呼吸的。在这幅景象中,人只是存在之一,从未与世界割裂;万物皆有表情。影片最主要的对白,是人与自然的交流,而雪山、森林、暴雪、狼群……也是故事的主人公。
拖拉机事故发生时,人类的表情凝固在惊恐与悔恨中,可溪流依旧汩汩流淌,森林仍保持着勃勃生机,牛群、羊群、马群也一如往常——大自然看见了一切,却从不为之改变。在这些“不变”面前,所有的变故,都显得轻飘;而万物之于自然,又何尝不是如此?如同一段悲怆的插曲,洛桑家在最痛苦之时,依旧参加了村里的祈福仪式,和村民们一起欢庆、舞蹈。那一刻,他们定然与雪山互相凝望,亦仰头向天空祈祷,或许,苦难不会因此消减半分,但是人活着最重要的,不就是心怀敬畏、坚守虔诚?
全片最激烈也最关键的一场戏,是豆拉伽与妹妹、妹夫的冒雪夜行。当时,他们刚协助卓玛给央金的妈妈顺利接生,而牧区还有两个病人在等待卓玛救治。可风雪实在太大,前行之路几乎寸步难行。最艰难的“跋涉”中,马匹突然受惊逃窜,狼群趁机围了上来……这是一场生命与生命的极限对话:人与狼平等地表达着“求生”的本能,激烈地对抗,各自爆发出最顽强的生命力。这场“大战”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天亮后,风停雪住,久违的太阳出来了,阳光抚慰了大地众生。
独特的镜头语言,构筑起一个悲喜交织、万物共生的世界。从这个世界里,我们终于看清了人所拥有的“三种灵魂”(亚里士多德之理论):植物灵魂,负责生长,无悲无喜,像高原所有植物一样,坚韧、顽强;感觉灵魂,人能感知悲欢喜乐,故而脆弱、故而善良,亦因此坚强、因此幸福;理性灵魂,源自人的精神,故得以与万物对话,突破局限、战胜苦难,最终超越自我。
直到影片的最后,央金也没能站起,但她用全力支起了上身,攀住木架,奋力向上、向上……这一幕,超越了所有现实主义表达。不觉间,观众也获得了一种心境的升华与抚慰——如同站在群山之巅,见到了宇宙,更看见自己。
责编:尹丽